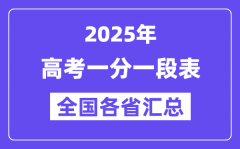|
臺灣作家羅蘭的《途中》就是運用客觀冷靜的敘述來表達他的哲理沉思的: 我喜歡屬于自己的時間,厭恨環境的牽絆。因此我總留戀那去什么地方的途中,因為它擺脫了一個個牽牽絆絆的環境,而尚未到達另一個牽牽絆絆的環境。這個途中的時間可以完完全全地屬于自己。 在寂寞的旅途中,我常感到前所未有的豐富,火車曾帶我認識大地,輪船曾帶我認識海洋。而在每天那單調熟悉的往返途中,我找到喘息和安靜的時間,讓我在那里嘗到擺脫之后的輕松。…… 所以,如果可能,我總是盡量拉長在途中的時間。我要利用這段時間想我一直沒有工夫去想的事。在這途中,我是陌生的個體,沒有人干擾我,沒有瑣事俗務需要我為了責任而必須去分心照顧。 我把自己交給腳步或車船,而我的心就可以逍遙自在地翱游在天地之間。 劉劍雄寫了一篇短文《糖人》,他的敘述方式也可歸為客觀冷靜的敘述,而且是很典型的。下面摘錄幾段: 天冷了……行人呵著熱氣依然行走匆匆。…… 前面,另一群小孩圍了一副簡便的擔子。從那熱鬧中我覺得溫暖。那是一副糖擔,一個流浪的糖人。…… 我一樣地在他面前站住了,看他用一小勺糖汁在大理石板上瀟灑地畫出各種動物,看他用笨拙的家什巧妙地點龍畫鳳。嫻熟的動作博得了孩子們的歡喜和起哄,紛紛捏著小票子要一個“鳥”或“馬”什么的。過路的小孩則扯住父親的衣角,大人們不自然地把手放在腰包里。糖人有些忙不贏,花樣卻在不斷更新。 我終于拗不過自己的好奇心,決定問他的來歷。 他是四川人,17歲學畫畫,終于意識到突破不了自己,于是流浪到東北做糖人。眼下北部太寒,就隨著風兒到了南國這片土地。 我想起畫家和糖人之間,想起了偉大與卑微的區別,藝術殿堂上,兩者之間太遙遠了。 一片落葉落在糖人的石板上,他用嘴一吹,葉兒打著旋飄落在一角的小溪中流走了。糖人還繼續著他的糖畫,仿佛根本與葉兒無關。我看著那片落葉,想了很遠很遠,很多很多。其實,落葉就是落葉,糖人就是糖人,我就是我,何苦要去編織那想像的網呢? 辭了糖人,我不再去想他的天涯浪跡了。只記起他的選擇和快樂,以及他一站又一站輾轉,隨便在一顆樹下或墻角擺上他的人生,不爭不奪,與人同樂,建著一個甜蜜的信念。 路對于他是不經心的,倒是他經心地在走著自己的路。 上面引用的《途中》和《糖人》都是運用了客觀冷靜的敘述方式。從上面兩篇文章中,我們可以約略明白,客觀冷靜的敘述方式和主觀色彩濃重的敘述方式正相反。其基本特點是: 第一,客觀地介紹人或敘寫事; 第二,取材慎重,內涵深廣; 第三,感受與情思滲透在字里行間。 |
熱門搜索:學習資訊 學習力資訊 學習方法資訊